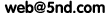歌曲 3
專輯
名 稱: 達(dá)菲;黛菲
所屬區(qū)域:歐美
Duffy出生于威爾士格溫思內(nèi)郡Lyln半島的Nefyn小鎮(zhèn),盡管父母并非鐵桿的樂(lè)迷,但Duffy還是通過(guò)家中少量的經(jīng)典唱片,以及聆聽電臺(tái)的音樂(lè)節(jié)目,讓她從小就有了立志成為一名Soul歌手的素材。不知道是不是應(yīng)了萬(wàn)事開頭難的老話,Duffy音樂(lè)人生的第一擊并不順利,由于耳聞目睹加上先天條件的雙重打磨,使得她的聲線扁平且有一定的沙礫質(zhì)感,也讓她很快就被唱詩(shī)班踢出了大門。不過(guò),內(nèi)向的Duffy,倒是很能耐得住寂寞,一邊在餐館打工糊口,一邊靜靜地等待著機(jī)會(huì)的出現(xiàn),直到有一天終于遇到了Jeanette Lee這位伯樂(lè),并由這位伯樂(lè)引薦給了更一位大伯樂(lè)——前Suede樂(lè)隊(duì)的吉它手Bernard Butler,她終于也有了機(jī)會(huì)向全世界展現(xiàn)她的歌喉。 有人將Duffy的聲線與Aretha Franklin比較,其實(shí)這是不太靠譜的,這樣做的可能,唯一的解釋只是推薦的人太想力捧Duffy,所以只能盡量把她和歷史上最為著名的Soul放到一起,以起到借前輩沾光的效果。其實(shí)Duffy的聲線條件更為接近的倒是Dusty Springfield和Petula Clark(達(dá)明一派的《Kiss Me Goodbye》正是翻唱自她的同名作品),融合了前者的沙啞、低沉、憂郁和后者這位英國(guó)秀蘭·鄧波爾溫和的Sunshine Pop,Duffy哪怕就是演唱普通的流行歌,都會(huì)因此而打上六十年代的標(biāo)簽,更何況是用Soul將這種懷舊與古典將懷舊加固呢?! 除了縱向之外,Duffy出現(xiàn)的時(shí)機(jī),也難免要讓人把她和橫向的潛在對(duì)手做比較。相對(duì)于醇厚中不失一點(diǎn)調(diào)皮活躍的Joss Stone、滄桑又頹廢的Amy Winehouse,以及新晉的擁有更趨多元平衡的Adele,Duffy的聲線似乎更為明亮和文雅,盡管Soul的騷味十足,但她卻不像Joss Stone和Amy Winehouse會(huì)被人誤以為是黑人歌手,因?yàn)樗谘堇[中,更多的會(huì)融入一些很Pop的成份去稀釋純粹的Soul元素,使音樂(lè)更趨向柔美與野性、明亮與黯黑之間的平衡。 專輯的同名曲《Rockferry》,由里到外都散發(fā)出一出六十年代的氣質(zhì),而不止是編曲與聲線的模仿,幾乎讓人懷疑CD或是MP3出了什么問(wèn)題,怎么跑出一種留聲機(jī)的音效來(lái)?英國(guó)單曲榜三連冠的《Mercy》則又呈現(xiàn)出Duffy韌性十足的嗓音特色,在六十年代伴隨著風(fēng)琴聲中響起的她的聲線,就尤如皮筋般韌勁十足,聽來(lái)格外具有嚼勁。專輯最后的《Distant Dreamer》在編曲上則似乎不那么舊了,甚至有了點(diǎn)Indie融合的意思了,但Duffy空間感很強(qiáng)的聲線,還是讓這首原本可以被Indie樂(lè)團(tuán)處理成或清新、或夢(mèng)幻的小品,演繹出一種掌聲響起來(lái)那樣的明星范兒,大氣十足。 那么,最后是不是該把時(shí)間和掌聲留給這位在聲線條件上天生麗質(zhì)的歌手Duffy呢?如果早五年,我想答案是肯定的。但經(jīng)歷了近幾年如此之多復(fù)古歌手的歷練之后,你就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,現(xiàn)在這股復(fù)古風(fēng),竟然也和更早一些的獨(dú)立風(fēng)一樣,在久而久之相同的大線條中,再難給人以獨(dú)特的悸動(dòng)。小爆發(fā)是有,但也只不過(guò)是集中在諸如唱功、味道這些細(xì)節(jié)上面,而音樂(lè)本質(zhì)中那種靈魂的顫動(dòng)卻依然欠奉。這也讓包括Duffy在內(nèi)的復(fù)古大軍成員,還是只能定格在優(yōu)秀歌手而不是歌者的位置。尤其重要的是,這樣的復(fù)古風(fēng)甚至還不如當(dāng)年的獨(dú)立潮更容易讓人看到點(diǎn)音樂(lè)未來(lái)的希望,說(shuō)句杞人憂天的話,在如今這個(gè)音樂(lè)資源匱乏的時(shí)代,我們還可以利用前人栽樹的成果來(lái)乘乘涼,但未來(lái)的未來(lái),我們又如何用音樂(lè)來(lái)介紹我們這個(gè)正在進(jìn)行時(shí)的時(shí)代呢? 更多>>